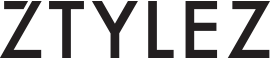每當提到「蛙王」郭孟浩,別人總會稱他為:行為藝術第一人、藝壇老頑童、概念藝術先鋒,甚或狂人。很多人以為他憑藉一身奇裝異服才在藝術界打響名堂,然而早在七十年代,在保守的社會氛圍下,他早以各種破格的實驗藝術進行創作。抵著一直以來別人對他的不理解與輕視,蛙王堅持劍走偏鋒,以身體作傳播媒介,選用不同類型的媒材打造各種實驗、雕塑、畫作、裝置等。一路走來半個世紀,如今他在藝壇的地位早已不容撼動。雖然年屆 74 歲,但他依然以精力充沛的姿態活躍在本地藝術場域。每逢蛙王有份參與的大型博覽會,他還是穿著一身「青蛙裝」遊走於現場,大玩特玩,樂此不疲。一件如此消耗心神的事卻持續進行了幾十年,到底他還在堅持些甚麼?
如今蛙王深隱元朗鄉郊,卻沒有因此與外界脫節。他持續創作,以藝術連結社群,甚至連自己的家,都被他的各種裝置佈置得像個小型博物館。從村落小徑延展家中一閣,每個角落都被「青蛙」圖騰佔據,宛如一片專屬於他的藝術領地。本集《藝城遊記》離開城市,跟隨蛙王深入由他一手打造的蛙林(Frog Jungle) ,希望藉由一片小小的領地圖個一鱗半爪,看看他窮盡一生都在打造一個怎樣的理想國度。
訪問當天,蛙王一見面便是以全套「青蛙裝」示人。八月炎夏,他穿著厚厚的針織手袖、頭上頂著假髮與帽子、頸和手上穿戴上不同飾物、戴著青蛙眼睛,手執拐杖,緩緩走進我們視野。一整天下來,他帶領我們參觀了他的「青蛙博物館」,又去了他位於牛潭尾的新家及工作室參觀,更即席為我們表演了一場水火交融的大型實驗藝術。縱然大汗淋漓,也不曾喊累。他說這麼多年都習慣了,眼神與口吻不會騙人,變裝後的蛙王其實也樂在其中。為著我們到來而準備的表演,他開心地說:「又可以玩一頓了!」
「我不只是做行為藝術」
天性好動又多「鬼主意」的郭孟浩,自小就不活在成規之下,別人討厭呱呱作聲的青蛙,在他眼中卻是無懼別人非議,自得其樂,如像他本人的自我投射。長大後,別人舞會只選一名女生作伴,他卻邀請全班女生出席,大家玩得歡樂,他自稱自己為「青蛙王子」。後來到了紐約生活,昔日的王子自然升級成王,自此他便以蛙王這身份自居,並在藝術界留下足跡。如今我們所看到的蛙王,其實都是從幾十年前慢慢進化而成。早在七十年代末,大陸改革開放初期,他已經在北京天安門進行塑膠袋裝置藝術。當時蛙王這身份還未成形,那次表演已經被納為中國有記錄以來第一項行為藝術活動。
然而對於這開創先河的成就,蛙王卻不以為然,他認為只是客觀條件將他的行為歸類,並沒有太大意義。對他而言,行為藝術就是一種有意念支撐的行為表演,加上無數個實踐的體驗,自然成了行為藝術。簡單而言,有意識與概念的生活,本來就是一個作品。他說:「我在 70 年代做了很多行為表演,於是別人便說那是行為藝術,但後來我做過很多雕塑、裝置、實驗,別人卻不提,到了 2000 年後,我的創作依然被定性為行為藝術,我卻不喜歡這種叫法。」一直被稱作「香港元祖級行為藝術家」,別人聽來如此崇高的名譽,在蛙王眼中,卻是把他困在一個狹隘的圈子。他笑言希望跟大眾澄清這一點,語氣中充滿著創作者的無奈。當然這並非是想跟行為藝術撇清關係,而是他多年透過不同創作媒介、表現方式、跟觀眾互動、即興表演等實踐,只是希望別人能留意到種種出位的行為背後,那些千錘百鍊的概念與對生活的反思。

在蛙王的作品之中,膠袋、紙張、竹片、空氣、水、火等都能成為創作媒材,甚至他自己的身體,也能成為藝術的載體。這一身看似累贅的青蛙裝一穿便是數十年,很多人都以為這種標奇立異的打扮是為了吸引別人注目,蛙王卻說:「我不是以奇裝異服吸引人。」由始至終,不論蛙王這身份,還是這一身打扮,其實都只是藝術的表現形式,他更渴望觀者能將焦點放在他的創作之上。
既然不希望別人只將他歸類為行為藝術家,那他自己又怎樣定性自己的創作?他說:「那是『會呼吸的生命體』。」當生物、死物、食物、人體都在他的加工下被重新賦予活力,在蛙王眼中看來,沒有成不了作品的物件,只要你不被常規所限,任何物件都可以是表現藝術的生命體。
「藝術要有開拓性,原地踏步是沒有意思。」
蛙王的創作意念跟他本人一樣獨特,他跟我們分享獨一無二的創作理論:「我的藝術主張就是『任次元』,意思就是指任何型、任何量、任何媒介、任何意念、任何維度皆可創作藝術 。」只有你想不到的,沒有他沒試過的。這樣說一點也不誇張,別人眼中的廢物,在他眼中卻是創作的好材料,他總有辦法將平平無奇的東西轉化,不論是破壞還是加工,物件總能擁有第二次生命。他說:「藝術要有開拓性,不要重複既有,原地踏步沒有意思。」蛙王的大型裝置看上去好像凌亂不堪,但其實他自有一套章法。他認為自己的作品雖然看似雜亂,其實亂中有序,後來他更建立起一套獨一無二的「混統美學」概念,意指混亂中見統一的美學,持續做下去,便成了具標誌性的風格。

在幾十年的創作路上,他不但沒有固步自封,而是通過不同的實驗和表演開拓不同可能。他的創作非常重視互動,持續多年的「青蛙眼睛計劃」依然進行。他邀請不同人戴上青蛙眼睛,然後為他們拍照,他逗趣地說那是「frog you 」,只要戴上他的眼鏡,就是把那人「青蛙化」。自古以來烏托邦就是理想世界的代名詞,如今有蛙王打造的「蛙托邦」,不同國際、身份、年齡的人戴上他繪製的青蛙眼睛,打成一遍,個個笑得開懷,無意中重拾都市人失卻的單純快樂。
「紙張是創意的載體,將紙張拋上天,讓創意在天空飛翔」
訪問當天,我們參觀完他的蛙林後,便跟隨他前往偏僻的牛潭尾工作室,蛙王特意為我們的到訪準備一場即席的表演藝術。水墨一直是他主要的創作媒界,但他從不喜歡正兒八經地用水墨繪畫。新工作室外正好有一片空地,讓他可以玩玩把戲。以往在博覽會或是展覽現場雖然亦會玩,但始終礙於安全性問題,無法盡興,連他自己亦為此次表演感到非常雀躍。

當我們還在思忖他能玩些甚麼,蛙王已經大肆地將過了膠片的畫作拋在地上,那是他在最近一個大型展覽中展示的作品之一。他毫不留情的將它們灑在充滿砂石的地上,繼而往地上鋪上多張大紙,隨後拿著幾瓶墨水肆意潑在紙上,然後著我們一起拿著一疊疊 A4 紙往天空拋擲。滿天飛舞的紙回歸沾滿墨水的地上,表面漫出墨水的痕跡。蛙王拿出水喉往天上噴水,地上的墨被暈開一片,原來純白潔淨的紙張被墨水覆蓋。最後他拿出火槍,將剛剛的一切燒成灰燼。
電光火石的過程中,他接連用一波又一波具衝擊力的行動打破我們對創作的想像。後來他解釋道,紙張是現代人承載創意的重要載體,我們將這些紙張往天空拋,就是讓創意能在天空中自由飛翔。最後紙張飄散落地,沾滿墨水,就如同他長久以來的創作實踐,不論有多放縱任性,多麼離經叛道,最後還是回歸水墨。在這一連串看似極具破壞性的行為中,其實他在無聲地重塑對水墨的構想。當我們拋卻束縛,將這些現成物損耗得不成形,才能打破既有界線,獲得真正的創作自由。
其實這並非蛙王第一次進行這個表演,但對他來說,這種實驗藝術講究的是臨場性,縱然概念相同,但每次的試驗都會受人力、環境、材料等因素而有所不同,背後考驗的都是靈活變通的思維與意念。最後地上遺留一片狼藉,還得花時間清理,但這場消耗性極大的表演如像他多年以來的創作實踐,化簡為繁,捨易取難。在他眼中,這種經過精煉的思考而做的表演才是真正他追求的藝術。即使並非每個觀者也能從他的表演中領會到些甚麼,但至少他在每次過程中亦堅定了自己的想法——儘管做自己理想的作品,即使曲高和寡。
「創作的價值不可以單以金錢來衡量」

蛙王天生性情乖張,不論在學習、創作、生活都自有一套章法,不被世俗規範。若說他在藝術上深受誰人啟發,不得不提水墨大師呂壽琨。蛙王自言早已把他當作父親般看待,就學期間,當老師教授同學用水墨作畫,蛙王已經想到要用活魚蘸墨,將牠們放在紙上擺動,形成「身體動能掙扎出來的痕跡」,結果被老師大罵一頓。後來呂壽琨去世,他亦有感自己的藝術在香港不受重視,便拋卻在香港的教職,遠走紐約發展。在美國一待便是十五年,期間不時拿出老師以前上課的錄影帶來聽,他說:「每次想到他已經離去,便會不期然哭了起來。後來在紐約重溫老師以前的一字一句,總覺得給予了我很多營養。」呂壽琨的教導啟發他往後都用水墨來創作,而這位水墨大師給予他的不只是水墨上的啟蒙,更是對藝術鍥而不捨、自成一家的追求。
創作是好,不創作是好。創作從來就都是一個很矛盾的過程。
蛙王在水墨路上另闢蹊蹺,備受質疑多年,最後的堅持與韌性使他終在現當代水墨路上站穩陣腳,成為藝術界一股不容取替的異流。

而時至今天,昔日受人摒棄的作品在藝術市場上都有價有市。蛙王參與過國際間數千個藝術項目,每天不間斷地創作,大型博覽會、香港美術館重開、M+ 視覺藝術館開張等藝壇盛事都會看到他的身影。然而,熱愛創作與玩樂的蛙王並沒有因為如今的地位而自命不凡。相反,他仍不時走到社區和街坊大玩特玩,更將自己的墨寶、作品隨手送給參與者。近半年,他在元朗開展一個「谷亭街之友」的項目,邀請街坊一起戴上青蛙眼鏡,更為他們每個人改了一個稱號,寫成蛙王獨有的「畫字」再送給他們,彼此玩得不亦樂乎,更被街坊們以「會長」相稱。
然而將作品隨意派發的行為猶如跟畫廊、拍賣行唱反調,我們問這不是讓你的藝術路更難走嗎?他卻淡然地說:「理論上的確是物以稀為貴,將作品賣貴其實是一種商業行為,但更高的境界就不是說這些。如果在作品中找到一個有內質、富有哲學性的啟發,那麼創作的價值就不可以單以金錢來衡量。」相較幾十年前,大眾對他的創作強烈排斥,如今苦熬 50 多年,能得到別人的理解與支持已是彌足珍貴,在藝術道路上逆行多年,痛並快樂,任何物質與名譽都不可比擬。
「我是一個有承擔的無形文化財產的工作者,不只是藝術工作」

作為香港表演藝術第一人,蛙王的出現的確史無前例地開創了概念藝術的生態,然而他本人又如何看待自己在藝術方面的影響呢?他表示:「其實歷代發生過這麼多精彩事,只是沒有被記載下來,我的創作其實都是些很皮毛的東西。」對於自身的藝術表現形式,他更自嘲說:「我就是最老套最笨的那個,弄到全身都是東西,滿頭大汗還在做,其實是很蠢的做法。但反過來看,卻成了最傑出那個,因為我從原始中重新走出來。在香港個個都是正常生活 ,突然間走出一個瘋狂的人 ,但在藝術層面來說是最獨特的。」
以前他曾經笑稱自己是「下個世紀的藝術家」,數十年前的創作走到今天才開始被接受,這位藝術先行者或許在心底裡都隱忍著難以言說的孤寂。

當初在紐約打響名堂,甚至被邀請回中國舉辦展覽,直到 1995 年回流,蛙王便不再離開過。他對於本地藝壇的貢獻不容置疑,但香港這片土地與當時被視作藝術大都會的紐約相較起來,可以說是從大水塘游回小魚池。到底香港這個地方能帶給他甚麼,使他甘於駐足在此?
他說:「我在香港接受上一代的文化教育,得到啟發不少。現在的創作就是跟社會的人互動,其實亦是在回饋社會。我相信慢慢做下去,將自己的藝術與文化在社會中傳承下去,某年某日便能育成一顆果樹,到將來便會有所收成,其實新一代的人才也是這樣出來的。」蛙王長久以來的創作為大家帶來無數歡樂,而今仍持續走下去的原因更是擔起了一份文化傳承的使命感,他認為現今所做的就是一種「無形的文化財產」,而他就是其中一位傳承者。
「蛙托邦是一個開心、快樂、理想的未來世界」

他跟我們分享:「做藝術真的不容易玩 ,置諸死地而後生都未夠,要死過幾十次後 ,在很困苦、艱難掙扎之後突然脫穎而出,出來的作品才有內涵和耐看。」這 50 年來 ,蛙王做過幾千個項目,每一個項目都全力以赴去做,他說:「只要你當它是家常便飯 便不會覺得辛苦 。」能熬出點成就,哪怕只是能引起別人星點關注,他自己也就快樂。
年過古稀,如今的蛙王不再如年輕時般「跳跳紮」,手執一支拐杖的他即便走得緩慢,但仍不時拿著相機、青蛙眼鏡、墨水走進社區,與街坊們玩在一起,邀請他們進入他所打造的「蛙托邦」,他說那是一個開心、快樂、理想的未來世界。當玩得累了,便回歸蛙林休息,繼續埋首創作。
最後我們問他想成為一個怎樣的藝術家,他想也沒想便應道:「快樂的青蛙,能快樂便好了。」他曾笑言仍向著 9 百萬件作品的目標進發。完成一天拍攝,我們陪他從新工作室回到屏山的家,一個月後,這個自成一角的蛙林恐怕就要面目全非,但我們知道他自有無窮的創作力,他對藝術的堅持使「蛙王精神」在每片曾踏足的土地上都留下印證。
蛙林遷址,重點從來不在於地方本身,而是藝術家創造快樂的本能。那個耗盡一生打造的「蛙托邦」不曾消失,如同他的藝術一樣,早已深入香港的土壤,種下永恆。
Executive Producer: Angus Mok
Producer: Vicky Wai
Editor: Ruby Yiu
Videography: Anson Chan, Andy Lee
Photography: Anson Chan
Video Editor: Anson Chan, Andy Lee
Designer: Tanna Cheng
Special Thanks: Frog King Kwok